2018年2月12日早上,一則令人震驚和悲傷的消息在法學(xué)圈的社交媒體上迅速傳開,題目上赫然寫的是“羅老師千古”。羅老師是羅豪才先生。他在北京大學(xué)法學(xué)院長期任教,一生中重要的職務(wù)還包括北京大學(xué)副校長、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、九屆和十屆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等,然而他自己最喜歡被稱呼“羅老師”。本人與羅老師交往最多的階段是他2007至2016年擔(dān)任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會長時期。
一、眾望所歸的會長
良法善治離不開人權(quán)的目標(biāo)和宗旨,所以說法治與人權(quán)密不可分。在這個意義上,羅老師的一生既是法學(xué)學(xué)者的一生,也是促進(jìn)和推動中國人權(quán)事業(yè)的一生。因為羅老師是中國行政法學(xué)的開拓者和奠基人,曾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“大法官”,還是民主黨派、僑界的領(lǐng)導(dǎo)人,既有深厚的學(xué)術(shù)素養(yǎng),又德高望重,同行們經(jīng)常說他是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會長最合適的人選了。
這里說的“最合適”不僅僅是資格和資歷,更是羅老師親身實踐的真實描述和概括。
羅老師擔(dān)任會長期間,卓有成效地促進(jìn)了中國人權(quán)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在他和學(xué)會的推動下,中國高校建立的人權(quán)研究機(jī)構(gòu)多達(dá)幾十個。全國建立了八個國家級的人權(quán)教育與研究基地。政府與高校人權(quán)教育研究機(jī)構(gòu)的溝通和聯(lián)系明顯加強(qiáng),人權(quán)教育和人權(quán)研究在中國逐漸成為“顯學(xué)”,日益繁榮。學(xué)會定期出版《中國人權(quán)事業(yè)發(fā)展報告》(人權(quán)藍(lán)皮書)和《中國人權(quán)年鑒》。他支持研究會每年舉行人權(quán)理論研討會、人權(quán)教育機(jī)構(gòu)經(jīng)驗交流會,出席會議并經(jīng)常坐在第一排從頭聽到尾,認(rèn)真記錄。他支持人權(quán)學(xué)者參與國家人權(quán)領(lǐng)域立法和政策性文件的制定;支持人權(quán)研究會“走出去”,與國外政府和民間組織、人權(quán)教育和研究機(jī)構(gòu)交流與合作。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創(chuàng)辦的“北京人權(quán)論壇”成功舉辦了八屆,已經(jīng)成為中國人權(quán)對外交流領(lǐng)域的一個品牌,每一屆都有來自東西方不同國家、聯(lián)合國等國際組織百余名專家、學(xué)者或者官員的參與,國家主席習(xí)近平曾經(jīng)為論壇的開幕專門發(fā)來賀信。
羅老師并非一位只安坐書房的人,相反,他一直強(qiáng)調(diào)調(diào)查研究,每年都要到不同地方看一看,足跡遍及祖國的東西南北。每到一地,他都與當(dāng)?shù)毓賳T和高校人權(quán)領(lǐng)域的學(xué)者進(jìn)行座談,傾聽大家的意見,并支持當(dāng)?shù)卦谌藱?quán)領(lǐng)域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、不斷創(chuàng)新。許多地方原來沒有人權(quán)教學(xué),特別是將人權(quán)作為敏感話題予以回避,德高望重的羅老師的到來和調(diào)研本身往往就形成一個有效引起當(dāng)?shù)貙θ藱?quán)教育、研究和實踐的重視的契機(jī)。他也不辭辛苦地到美國等西方發(fā)達(dá)國家、古巴等發(fā)展中國家進(jìn)行訪問,與政府官員對話,與學(xué)界、僑界的老朋友、新朋友對話和交流。他的學(xué)術(shù)涵養(yǎng)、人格魅力和領(lǐng)導(dǎo)人氣質(zhì),使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的工作有條不紊,成效顯著,贏得了從國內(nèi)到國外廣泛的尊重與好評。
二、引領(lǐng)發(fā)展的法學(xué)家
羅老師一直在北京大學(xué)指導(dǎo)博士生,而且筆耕不輟。他的專著《軟法亦法——公共治理呼喚軟法之治》2011年獲中國法學(xué)會中國法學(xué)優(yōu)秀成果一等獎,該書也翻譯成多國語言文字在國外正式出版;在報刊和學(xué)術(shù)雜志上,近兩年都能看到他自己或者他與同事共同撰寫的學(xué)術(shù)論文。
羅老師在學(xué)術(shù)界的地位和影響,并不取決于他出版和發(fā)表的專著與論文的數(shù)量,而在于他在學(xué)術(shù)思想上的先鋒和引領(lǐng)作用。中國的社會治理長期以來呈現(xiàn)一種“大政府和小社會”的特征,中國“官”與“民”的關(guān)系怎么處理,中國的行政法向何處去?就此,羅老師率先提出了“平衡論”的行政法的主張。他關(guān)心中國行政法的理論與實踐,尤其是司法實踐。他推動了中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、修改和實施。2013年12月,我和研究會的其他同事陪同羅老師接受鳳凰衛(wèi)視“名人面對面”節(jié)目的專訪,結(jié)束時主持人吳曉莉請他為節(jié)目題寫一句話,他寫下了“為了權(quán)利與權(quán)力的平衡”這句話。
進(jìn)入新的世紀(jì),如何推進(jìn)依法治國,如何讓制定了的法律真正付諸實施,實現(xiàn)立法的目標(biāo),追求法治的目標(biāo)?羅老師率先在北京大學(xué)建立了軟法中心,提出了“軟法之治”的主張。與傳統(tǒng)的國家治理模式相比,他強(qiáng)調(diào)柔性治理,強(qiáng)調(diào)發(fā)揮基層和民間以及專業(yè)力量的積極性、主動性,強(qiáng)調(diào)非國家正式立法的社會軟規(guī)則的治理。他的主張是當(dāng)下加強(qiáng)和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的政策和理論的先驅(qū),他也成為世界范圍內(nèi)在法律領(lǐng)域倡導(dǎo)軟法研究與實踐的代表性人物。全國各地陸續(xù)成立了多家軟法研究機(jī)構(gòu),在全國范圍內(nèi)還成立了跨學(xué)科的中國行為法學(xué)會軟法研究會。因為本人結(jié)合國際法和國內(nèi)法對人權(quán)領(lǐng)域的軟法進(jìn)行了一些研究,羅老師推薦我參加了這個研究會,還擔(dān)任了副會長。
他培養(yǎng)的許多學(xué)生是中國高校、法律實務(wù)部門的佼佼者,可謂桃李天下。我認(rèn)識的一位他的學(xué)生當(dāng)年在南方某地方院校學(xué)習(xí),給時任北京大學(xué)副校長的羅老師寫信,表達(dá)自己的見解和愿望。羅老師不僅親自回信,還給予殷切的鼓勵,這位學(xué)生現(xiàn)在已成長為北大的教學(xué)骨干。我由衷地佩服羅老師的識人能力和鼓勵、培養(yǎng)年輕人的精神。他不是以一己之力,而是以自己和周圍更多人的集體的努力推進(jìn)中國法學(xué)、法治與人權(quán)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
三、寬以待人的仁者
羅老師總是能夠看清社會發(fā)展的方向,能夠做出引領(lǐng)性的理論判斷。不過,他絕不是一位咄咄逼人的權(quán)威,相反,在他的身上,你總能感受到長者的仁慈和寬容。在小型會議包括在外事活動中,他都經(jīng)常讓所有參加者都發(fā)言、表達(dá)自己,寧肯自己少講話,一個都不落下。他喜歡傾聽,在筆者看來,似乎到了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地步。有的研討會是冗長的,他七八十歲的高齡,竟然能夠聽到底、記到底,而且他并不會隨便插話或者干預(yù)。有的討論,特別是年輕人的課堂討論、非正式會議上的發(fā)言,可能是幼稚、偏頗甚至是無禮的,年輕人對羅老師可以不必客氣,說的觀點可以是不同觀點、批評他的觀點,他都會微笑傾聽。
在工作上,羅老師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,而且總強(qiáng)調(diào)集體努力和團(tuán)隊攻關(guān)。有一次,我跟羅老師一起到外地調(diào)研,中巴車上,一路顛簸,他一直在跟我討論軟法問題。羅老師經(jīng)常會跟學(xué)生或者研究會的同事分享他最近發(fā)現(xiàn)的新研究材料或研究動態(tài)。他會親切地說,臺灣地區(qū)的學(xué)者,還有哪國的哪位學(xué)者又出新作品了,你們要讀;學(xué)者來北京的話,要交流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他的閱讀量,包括網(wǎng)絡(luò)上獲得的信息量,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許多年輕人。
在國內(nèi)外,我見過許許多多對羅老師特別敬重、尊重的人,他們是學(xué)生,是法官,是行政官員,是媒體記者,或是普通的百姓。我也見過有人的確是因為不認(rèn)識、不懂得等原因,當(dāng)面無心冒犯過他的人,但是,我沒有見過他生氣,他不計較個人得失、不計較刻板禮節(jié)。相反,他時常會替別人著想,善意地“配合”遇到他的人、下屬或者學(xué)生。他能看懂別人的心思,主動讓想跟他合影的人一起合影,他會主動向接待他的服務(wù)員、廚師致謝。
早年在新加坡追求自由與正義,羅老師坐過英國殖民者的監(jiān)獄?;氐阶鎳?,他是堅定的愛國者,成為資深的法學(xué)家,大法官,重要的民主黨派——中國致公黨中央的主席,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機(jī)構(gòu)之一——全國政協(xié)的副主席。羅老師見證了中國民主、法治與人權(quán)的發(fā)展,領(lǐng)導(dǎo)了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級人權(quán)研究和促進(jìn)機(jī)構(gòu)——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的工作,促進(jìn)了中國行政法學(xué)、人權(quán)法學(xué)的進(jìn)步。
羅老師對人權(quán)和法治事業(yè)、教育事業(yè)做出了巨大貢獻(xiàn),今雖離我們遠(yuǎn)去,風(fēng)范長存,將永遠(yuǎn)激勵我們前行。 深切緬懷羅老師,中國人權(quán)研究會一位偉大的會長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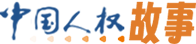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102003980號
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102003980號